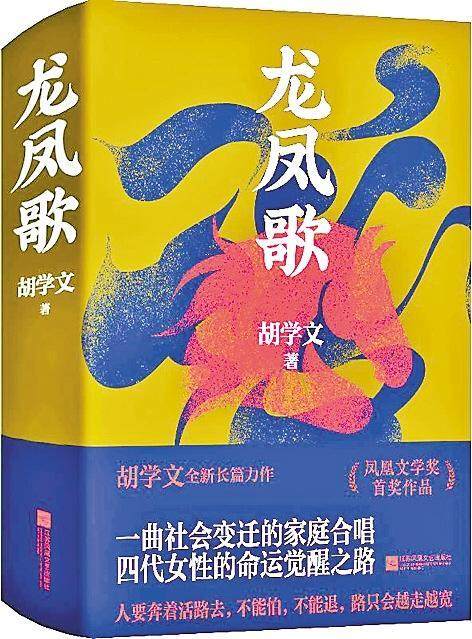
翻开胡学文长篇新作《龙凤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边看边思索一个问题:在其上一部长篇小说《有生》之后,这部小说何以会“发生”?
相比于《有生》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和或隐或现的紧凑主题,《龙凤歌》虽出版成一册,但内文分为上下两卷,似乎庞大的体量并未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上卷马秋月的婚事、打月饼分月饼的经过,下卷朱丹之死牵连出朱红、朱灯这一对龙凤胎的人生经历等,这些情节都依靠人物串联起来。有梦游症的马秋月和会讲故事的麻婆子,似乎分享了《有生》里“祖奶”的身份;从马秋月的二姐和二姐夫曲风身上,甚至可以看到作者获鲁奖的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里乔丁和“凤凰女孩”的影子。这一切成了笔者沉浸在故事里的理由。技巧显然不是原动力,弥散在众多人物和芜杂日常中的乡村伦理及其对人性的鉴照,或许才是作者久积心中、欲吐之而后快的“块垒”。
《龙凤歌》以作者故乡张家口坝上的乡村生活为背景,讲述了马家和朱家几代人的身世命运和人生悲欢。上卷以朱光明、马秋月一家人的生活为中心,通过贫苦日子里的相濡以沫,展现他们和子女朱红、朱灯、朱丹各自的性格。下卷以处理朱丹车祸身亡事件为核心,勾连起三兄妹的生活经历,呈现他们在现实中的挣扎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小说建构起一个复杂的乡村生活网络,嵌入书名的“龙凤”二字,从人物设定上指向朱红和朱灯这对龙凤胎姐弟,但在隐喻意义上则涵盖了这个网络中的所有人——朱红和朱灯凭借个人努力走出村庄,是为“龙凤”;马秋月夫妇和马家、朱家的兄弟姊妹等,各自在艰苦岁月里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亦堪为“龙凤”。作者笔下的“龙凤之歌”,实则是尘世男女求生求爱、求真求暖、求富求变的更唱迭和。
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生活事无巨细的书写,使《龙凤歌》充满现实质感,给人“毛茸茸”的感觉。这种感觉仅靠民间风物和生活情景构成的“物质外壳”是无法实现的,它还要有对乡村伦理精神的精准把握和抒写。小说对此有细腻表现,其中最出色的是马秋月打月饼过程中,对人物心理和行动的生动描写。3岁的朱灯见了大有女人给的半块月饼而能开口说话了,马秋月认定“月饼是吉祥物”,决意要在中秋节前打月饼。但拮据的家里没有充足原料,于是她托关系去供销社借糖,去被传说睡觉前“要用扫帚扫牙缝”的大姐家借油。在大姐家,马秋月觉得难以说出此行的目的,“那句话就在舌尖嵌着,或许长得太牢了,嘴唇轻启两次,竟未拽动”;当她终于把话说出来,“仿佛耗尽了力气”“有些虚脱,但也就是瞬间,很快又充足了气,仰起脖子,好像不是来借,倒像来要账”。小说写活了一个性格内敛的农村女性向别人求助时的手足无措。月饼打成后,很快又陷入如何分配的难题,分来分去,二十个月饼只剩了一个。小说写道:“中秋节,一家人守着一个月饼,马秋月有些酸。”小说通过这件事写出了乡村伦理的微妙。而面对事件的结果,相信“酸”的不仅是马秋月,还有每一个读者。
《龙凤歌》里写到的生活已经远去,当辨识乡野植物、种地养马、打月饼等生活经验以知识的形式出现在小说中时,它们不仅为后来者指示了进入和理解经验的路径,也成为人物性格的具象化象征。朱光明和朱灯的经历都是典型的例子。朱光明会拉二胡,因此有了与马秋月的姻缘。成家后,朱光明从霍木匠那里学来了手艺,解决了养家糊口的问题。霍木匠传授给他《鲁班经》,不单纯是技艺的传授,更有精神的传承。从此,把玩和制作榫卯等木构配件,尝试做一个“九脊顶戏楼”模型,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享受。因为这个爱好,他在生活的重压下获得喘息的机会,从“讨生活”的工具变成一个“有自我”的个体。朱灯中师毕业后到乡中教书,这一段经历隐含着某种个人才情和性格上的可能性。在后文中,朱灯因写字漂亮又有写作才能,被借调到乡政府工作,从此开启了从乡村教师到省报编辑的人生之旅。长期的乡村生活和基层工作,使他面对变故应对自如,却在处理朱丹的事情时畏首畏尾——在亲情面前,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反倒成为负累,一个从底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形象呼之欲出。
从乡村伦理到城乡冲突,从生活的困难到命运的困厄,从必然的情理到无法预设的荒诞,《龙凤歌》中对现实经验的密实书写,让叙事充盈着审美气韵,但这并不构成对现实的“再现”。从情感色调上看,作者笔下的生活是沉重、晦暗的,但小说并没有让人读得喘不过气来,而是颇有飘逸和温暖之感。这恰恰彰显了作者的叙事功力。为了消解幻灭感,作者赋予了人物多样化的道德情感、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以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增强了乡村的丰富性。
书中的人物生存艰难但没有被困难吓住,他们不断与现实和命运搏斗。马秋月面对唯一的一个月饼,并未觉得未来无望,“看着朱灯和朱红你一言我一语,虽不在一个节奏上,但到底能对话了,她的心又有蜜汁滴出来”。朱红性格刚毅,丈夫刘长腿的一次次背叛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婚姻破裂后开裁缝店并培养子女成才,在处理朱丹事故时显现出追求真相的执拗。“她生在和平年代,但始终在战斗,生来如此,命中注定”,这虽是作者对这个命运悲苦的女性一生的总结,但又何尝不是对所有人的评判呢?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而奋斗,就连死去的人也是如此——朱灯为了不让父母知道弟弟死去的真相,为他虚构出一套并不存在的生活。在亲人们心里,他依然在世上过着自己的日子。
在传递爱、温情和坚韧的同时,小说也交替展开对人性和陋习的批判。武三的横行霸道、宋大肚的趋炎附势、刘长腿的色欲迷心、刘栓的明哲保身等固然可恶,但马天不问马秋月一句就将她许配给朱光明,也是封建思想在作怪。当然,在小说创作中,批判也是抒情——胡学文在《龙凤歌》的创作谈中说:“这是一部为情而写的小说,不止个人感情。哪怕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深度。”但事实是,当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按照生活规律走向各自的命运时,其意义在因果逻辑和个性与情感的交织中自见,作者也无法阻挡。(桫 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