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根据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改编的同名电影和电视剧先后官宣阵容,又一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将以影视剧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近年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掀起影视化热潮。从《平凡的世界》《推拿》《白鹿原》,到《人世间》《繁花》《北上》,这种影视改编并不是简单的IP移植,而是在文学与影视两种艺术媒介碰撞中,完成了文学经典的“二次生长”。这些影视剧从不同维度诠释了文学经典如何在影视改编中实现新的意义生成。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为影视注入精神根脉,影视为文学开辟传播路径,二者在对话中让经典从“完成时”的文本扩展为“进行时”的生活和审美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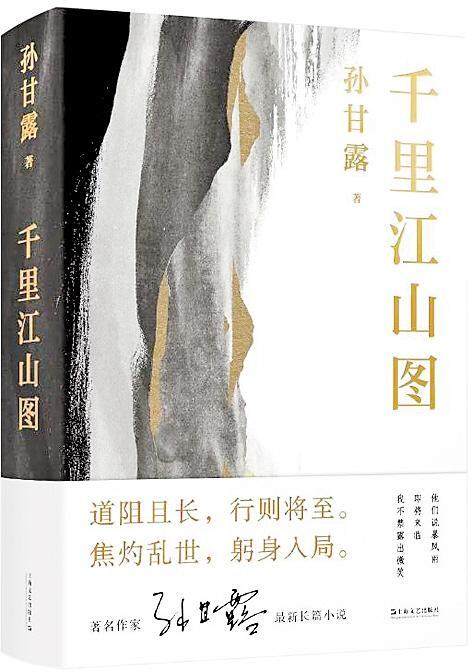
中国当代影视改编的发展脉络,是时代文化和精神的精准反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莫言《红高粱》等文学作品经过改编后透过银幕直抵人心。21世纪以来,一大批网络文学改编作品的“爽感”叙事逐渐席卷屏幕。快节奏的叙事、主角光环下环环相扣的情感模式,精准呼应了大众的阶段性审美需求。然而单一的“造梦”机制,不免令影视创作滑向精神快餐。近年来,茅奖作品逐渐成为影视改编的“富矿”。改编轨迹的每一次转向,都携带着时代精神和社会审美变迁的印记。
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虽有高质量文本的优势,但要在小说的文学性、经典性与影视的娱乐性、大众性之间找到平衡,则需要主创团队对文字有深刻理解,对影像有精准把控,能够将严肃文学转化为大众更容易理解和共情的表达。
《暗算》的改编展现了类型化与文学性的深度融合,超越了传统谍战模式的悬疑依赖,增加了更多对信仰和人性的追问,诠释了从“欲望的人”到“意志的人”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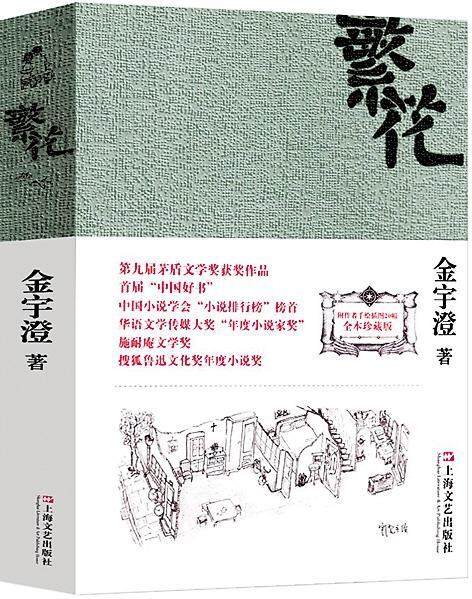
《平凡的世界》原著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精神图谱和艰辛跋涉历程,在电视剧中呈现时对整体的叙事温度有所调整,具象为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样处理既保留了原著的故事和人物性格,又强化了观众对主人公面对平凡人生努力奋斗的共情。
《人世间》的改编同样深谙此道。原著中周家三代跨越五十年的人生起伏,串联起知青下乡、恢复高考、国企改制、旧城改造等历史节点。电视剧改编时侧重家庭关系的细节描述,将小说中的叙事和时代感交融在更日常的生活肌理中,调整了部分人物命运的戏剧张力和性格力量。比如女主人公郑娟在小说中是被动承受生活和命运的角色,剧中则增加了彰显人物主体性的情节。
《繁花》的改编更像是一场充满张力的美学角力。金宇澄的沪语原著浸润着市井烟火的粗粝质地,王家卫则以美学重构这份市井史诗。剧中至真园的霓虹灯在雨幕中晕染成旧胶片般的暖黄,排骨年糕的热气在慢镜头里凝成白雾……这些画面是导演用镜头语言对沪语小说的二次创作。当小说的市井气与导演的镜头美学碰撞交融,最终呈现的视觉效果让《繁花》成为当下影视剧中独特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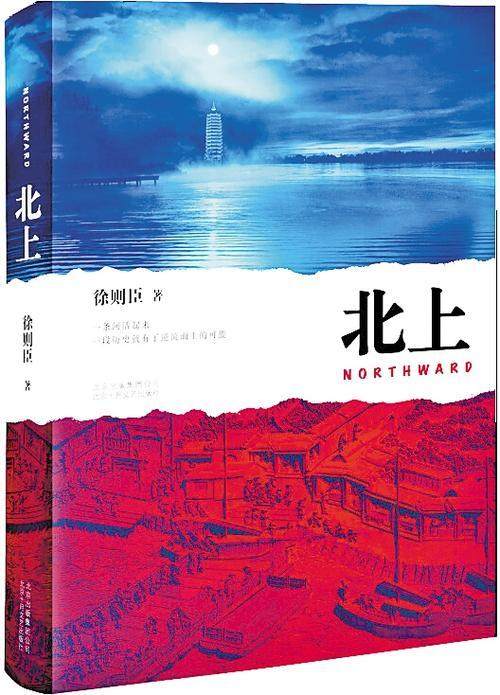
《北上》原著小说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历史与人物命运。同名电视剧则在故事结构、人物关系上进行了重构,强化当下与未来的故事性和烟火气。剧中运河文化成为当代人对话历史和确认自我的路径。
这些作品的改编各有各的难度,亦各有各的转化之道。或融类型,让悬疑承载哲思;或调温度,让苦难落地成日常;或融风格,用镜头重述市井;或重构叙事,让历史走进当下。
茅盾文学奖评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有50余部获奖作品。这些作品既标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更串起了经典生长的脉络。何为经典?或许没有绝对的量化标准,却有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普遍共识:它必须有厚重的精神纵深,能让青少年读出青春的热血、中年读出生活的沉郁、老年读出岁月的回甘,让农民在孙少安的砖窑前看见自己的影子,让工人在周秉昆的挣扎里感受到命运的温度;它必须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读者能在文字中找到自己的生命投影;它必须是人类精神“公约数”,在反复阅读中被激活为个体确认自我的镜子、对话世界的桥梁。经典的本质不是成为完成时的标本,而是始终处于进行时,它们在代际阅读中被重新诠释,在多元阐释中被赋予新质,在艺术转化中获得更辽阔的生长空间。
经典的生命力,正来自这种开放性与未完成性,需要一代又一代读者用生活与生命经验去反复再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影视改编的特殊价值愈发凸显。它用视听语言让“未完成”的经典文本跨越媒介边界,在大众传播中获得新的生长动能,在不同媒介中获得新的意义呈现,不断更新着表达方式与精神内核。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最终要落实在被接受和被认同上。影视改编通过情感动员的力量,将读者对文本的理性认知转化为感性共鸣。文学经典的深度往往源于其对人性、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但这种洞察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与思考能力。而影视改编通过人物命运的具象化、情感冲突的集中化,让观众在代入感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经典作品的精神内核。那些经典文本纸页间沉淀的语言艺术的厚重和深刻,借由视听艺术的声色光影,持续实现蓬勃的“二次生长”。(金赫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