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批评家吴媛的文学评论集《“现在”的现场》,关注当代文学的创作现场和批评现场,涉及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网络文学、创作综述、文学访谈等多个领域,以“处身的在场”“女性的在场”“地方的在场”三重维度,坚持文学批评“鲜活”在场,触及文学深层肌理,把握时代脉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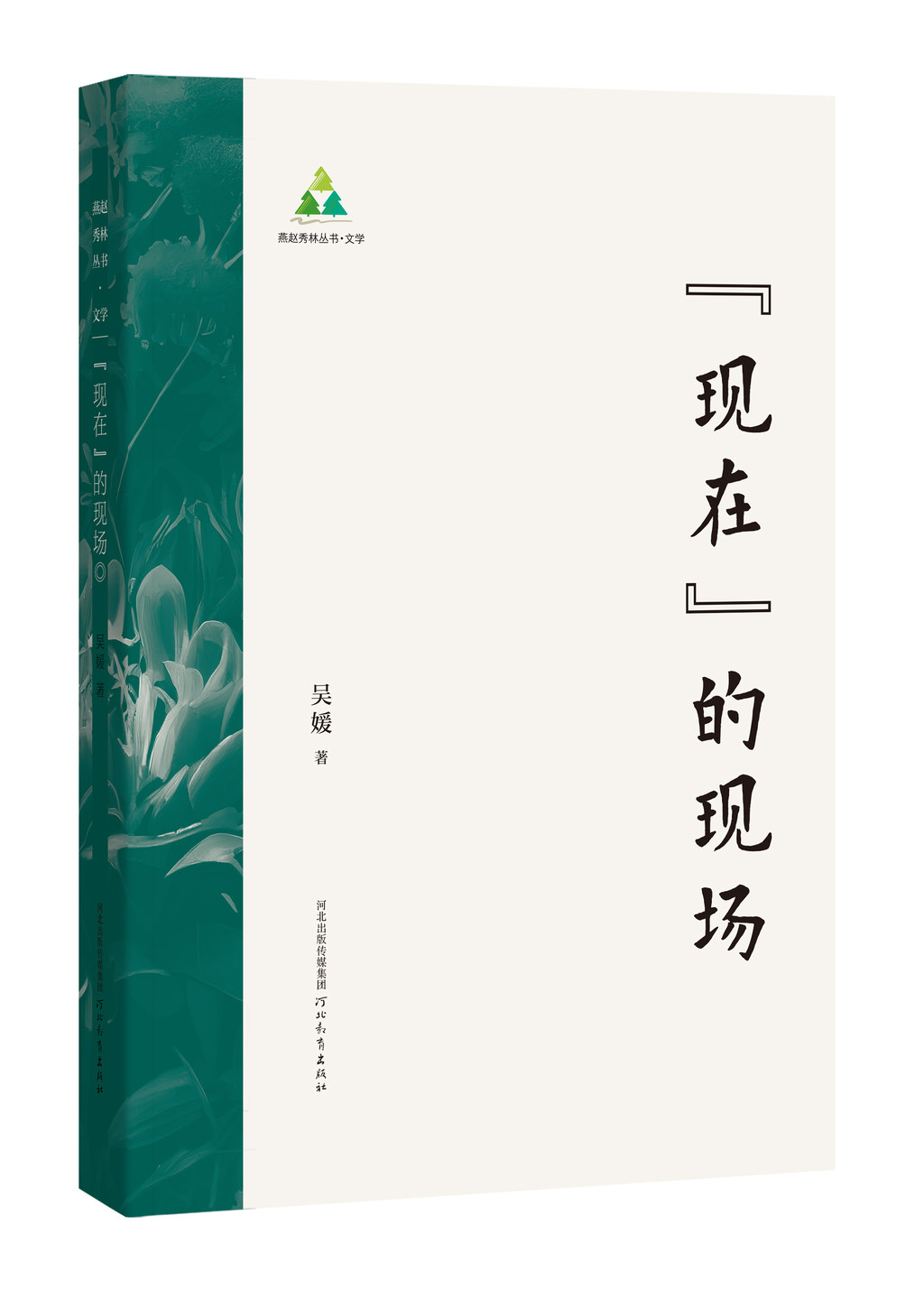
吴媛是一位具有跨界经历、多重身份的青年批评家。她既有古代文学的功底,又对现当代文学有深入研究,还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她既深入创作群体,又保持文学批评的审美距离。她的文学批评具有一种独特的在场性,能够在文学的多重现场和不断转场中,保持不同视角的介入反思。她看到了主旋律创作的多样话语表达,看到了民间写作的进阶与规训,看到了“燕赵七子”诗歌的边缘与坚守,看到了基层作家的默默匍匐与执笔飞翔……
评论集分为“诗意之所来”“叙事的魅力”“对话与升华”三辑。在“对话与升华”部分,吴媛通过与当代知名学者、批评家的访谈对话,一起探析批评家的角色特征。知名学者张莉的文学选本带有强烈的个人趣味,坚持一种选家的个人“偏见”;诗歌批评家胡亮着重区分诗人的趣味化和选家的非趣味化,强调选本偶然性中的客观必然性;诗评家王士强则在“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辩证关系中,强调批评实践的公允客观,并对自我的局限性保持警惕,进而将文学置身时代,突出批评家就是给欲望的列车踩刹车的人。吴媛在访谈对话中,始终对文学批评以及批评家身份保持一种“处身的反思”,从而让文学批评立场的多重样态跃然而出,留待深思。
作为一位女性批评家,吴媛对文学现场的观察直面“女性的在场”,观察女性书写,探讨女性处境。评论集第一篇便是《现代性视域下的新时期河北女性诗歌》。在现代性精神与女性主体性的相互呼应中,勾勒出河北女性诗歌的独特景观。河北女性诗歌“温柔敦厚”的诗风,是基于中国传统女性美好形象的当代投射和自我期许,但同时也容易陷入单一化审美、私人化叙事的自我束缚和同质窠臼。此外,在阅读李磊诗歌时,吴媛敏锐发现其在现代经验与复归抒情传统之间的不确定性,同样游移的还有其诗歌写作对自身女性立场的怀疑和重建。运用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处境视角,吴媛探析了80后女作家左小词的小说《棘》,反思了其女性乡村乌托邦的想象及遮蔽,这是现代性洗礼下传统民间集体无意识的冲撞。
“现在”的现场,是一种作为时代精神“现在”的时间概念,也是一种作为社会语境“在场”的空间概念。吴媛在评论集《“现在”的现场》中,格外突出了一种地缘处境。评论文章题目常常涉及城市、山村、乡土、故乡等空间意象,如《新世纪以来诗人的城市群落式生存》《山村孩子的音乐世界》《讲述乡土,抑或自我》《出离与重返:故乡是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等。
吴媛格外凸显了“地方的在场”。例如《现代性视域下的新时期河北女性诗歌》《当代河北文学的个体书写与家国情怀》《边缘与坚守:“燕赵七子”诗歌阅读印象》等。实际上,这种“地方的在场”作为一种文学空间,贯穿在上述关于城市、山村、故乡的地域处境的思考之中。
吴媛对参与空间建构和空间生产的河北地方文学不乏反思。一定程度上,河北的文学作品在建构地方文化想象上比较薄弱,其地域特征不甚明显,作家的地域认同感与共同的文化意识并不强。即使类似“新保定诗群”的地方在场写作,吴媛也犀利地指出,这种地方诗歌的“异托邦”,似乎并未跨越城乡二元对立套路的空间想象,也并未超越地域限制抵达诗歌经验的生命本真。在地方化与同质化的悖论张力中,未来有待更强的诗歌动力和更高的诗歌成就。
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作品可以一键生成,文学评论可以通过算法产生。作为人学的文学活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人工智能的训练现场。那么,置身时代现场,文学何为?批评何为?可以说,吴媛的这部文学评论集以一种文学批评的鲜活立场,一直在场。
评论家简介
吴媛,河北保定人。曾荣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在《文艺报》《博览群书》《诗选刊》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20余万字。
(张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