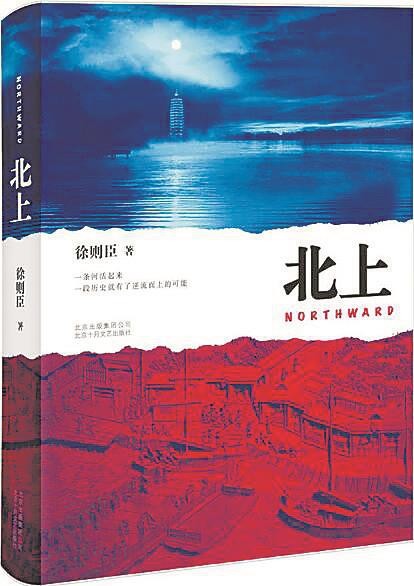
随着电视剧《北上》的热播,运河岸边花街小院里的人间事与烟火气再度唤起人们的往日记忆,而花街所在的江苏淮安运河古城正是原著作者徐则臣的故乡。“花街”是徐则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场景与背景,恰似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路遥笔下的双水村、梁晓声《人世间》中的“光字片”。每个时代都需要小说家充当故乡事的讲述者,在文字中保存那些即将消逝的风物。而从鲁迅的绍兴乌篷船到双雪涛、班宇的东北老工业区,小说家们一直试图以虚构抵达最真实的故乡,进而完成三重使命——打捞记忆、安放乡愁、以故乡为原点去理解和感受整个世界。
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是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小说气韵沉雄,以“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当徐则臣要以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面对时间和空间如此庞大的历史与现实,以怎样的叙事策略和切入角度进入浩如烟海的运河往事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徐则臣选取了一个重要角度——从自己最熟悉的故乡风物进入历史和叙事。小说对运河沿岸风俗和几代船民日常生活的描摹,超越了传统民俗志式的陈列,通过文学手段重新挖掘、保存和重构关于故乡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可能被遗忘或淹没的部分,在对记忆的打捞中,凝结成具有作家个体辨识度和普遍阅读价值的经典作品。这种打捞固然包含抢救性的文化书写,本质上更是通过文学重构赋予记忆新的阐释维度,令人想起沈从文《边城》《长河》中,那些以诗性笔触打捞起的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故土记忆。两位小说家的写作相隔将近一个世纪,但那些被打捞的记忆碎片,都在文字中重新生长为真正独属于一个地方的风俗史与心灵史。
大概没有哪个词能如“故乡”这般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中占有足够的分量。而关于故乡的书写又往往是一个作家离乡的产物。鲁迅笔下的周庄、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徐则臣笔下的花街……离开故乡,它才真正成为作者的审美和书写对象。一个人,从故乡出发,奔向外面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反复怀疑和确认自己,重新打量故乡;他决绝地逃离故乡,到世界去,回身时却仍忍不住乡愁满腹。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故事的经典一刻与惊鸿一瞥,近百年来一直在发生和演绎。身处他乡时,精神上稳定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会令一个人自然而然思念自己的出发地。而一旦肉身真正重返故土,却往往发现自己已是半个外乡人。这种踟蹰和纠结恰是故乡叙事的生发时刻,用学者王德威的话说就是:“故乡之所以成为‘故乡’,亦必须透露出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象魅力,当作家津津乐道家乡可歌可泣的大事时,其所灌注的不只是念兹在兹的写实心愿,更是一种偷天换日式的‘异乡’情调。”某种意义上“乡愁”是被创造出来的,故乡是被离乡之人想象和建构的。
徐则臣有部短篇小说集《如果大雪封门》,收录的17篇小说中大致处理和表现的是两种经验:在故乡以及漂在北京。在《梅雨》《最后一个猎人》《忆秦娥》等小说中,故乡花街的风土人情、自然风物在一种绵密悠长、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中渐次清晰,那些繁复细碎的花街故事,运河边的乡村传奇,是作者彼时彼地的美好回忆,更是此时此地的无尽乡愁。《如果大雪封门》则是关于“京漂”生活的一唱三叹。其中外地人对北京的向往与奔赴,以及重新落地生根过程中精神与现实的双重艰辛,却又是基于故乡的视角在展开。作家梁鸿曾以“乡愁”来解读和分析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她认为“乡愁”不是一种实体存在,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定,它是自古以来产生于任何怀乡之人头脑的感情,而在现代性视野观照下,乡愁有了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既是一种具体的精神指向,也是一种‘方法’”。徐则臣笔下从“花街”出发的一代人的精神叙事,正是以“乡愁”作为观照世界讲述自我的基本方法。
当然,对大部分小说家来说,“乡愁”的炙热与真切并不是他们的核心叙事的目的,那些经典的故乡叙事,其实或隐或显都包含对更远、更宽阔之处的遥望,书写故乡的优秀作品中都有一条通往世界的密道。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故乡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不仅是往事和记忆中被安放的乡愁,更是“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就如同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题记中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尽管他在创作之初可能只是想写下故乡的人和事,可当“双水村”这个被作家创建的“自成一体的天地”逐渐枝繁叶茂、血肉丰满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那里已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实验室与演绎场。孙家兄弟的人生选择与命运沉浮,固然折射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缝隙中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碰撞的阵痛,孙少安从生产队长到乡镇企业家的蜕变轨迹,更暗合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脉络。
近年来“新东北写作”浪潮中,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创作正是这种故乡叙事的典型代表。他们笔下的故乡既是具象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又是中国社会在时代前行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在《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生吞》《逍遥游》等作品里,读者总能看到衰败气息里的工厂和宿舍区,以及录像厅、舞池等这些特定时代的东北景象。而作为成长于老工业基地企业改制背景下的80后一代,这些小说家的叙事背景总是那个时代一度踌躇失措的故乡。他们以自己记忆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和事为叙事基点,讲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国企改制过程中父辈这一代人的命运与挣扎,同时将地域经验转化为对于时代变迁、社会变动更具普遍性和深刻度的演绎。他们作品中所描摹的破败厂区、废弃澡堂、冰封河面,是后工业时代人的现实与生存困境的隐喻。这种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故乡叙事和地域文学的框架,使东北升华为观察世界的棱镜。他们的写作证明,真正的故乡叙事不是回望的挽歌,而是以地方性经验为切口,打开通往人类共同境遇的叙事通道。那些冻结在东北记忆里的疼痛与尊严,最终都将成为丈量整个时代精神维度的文学坐标。(金赫楠)

2025年3月28日河北日报《文化周刊》11版文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