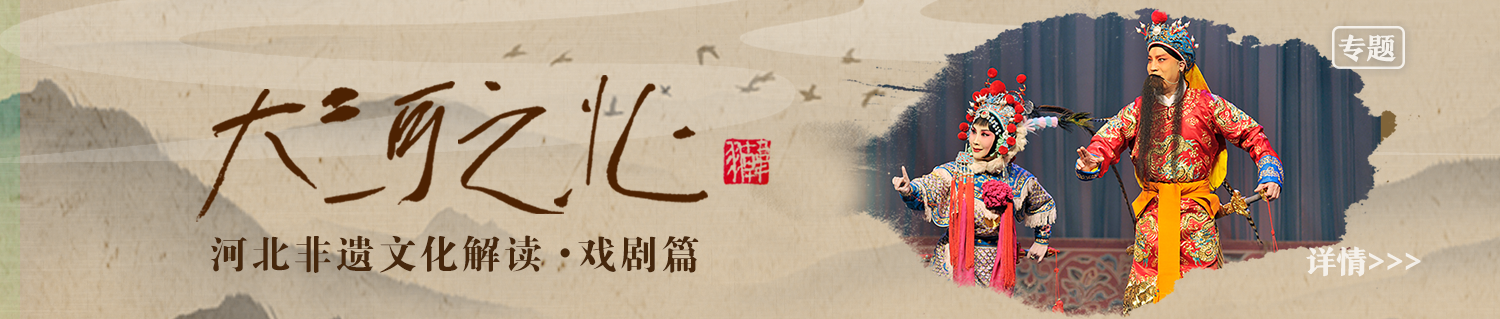1月19日,武安傩戏《吊黑虎》上演,掌竹(右二)介绍剧情。河北日报记者白云摄
人神共舞,沟通天地祈福迎祥
“看我变身!”1月17日,武安傩戏传习所,开始排练的丁建宇把手里抱着的面具一戴,架势一拉,就完成了帅小伙儿到神灵赵公明的转变。
赵公明面具长约40厘米、宽30厘米,头顶是长长的雉翎,下面是灰白毛发、巨目红唇、棕脸白牙,大红绸子花额头一束,显得端庄威严。
“戴面具这种原始的戏剧化形式,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主要特点之一。”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周大明说。
傩戏发源于祭祀。祭祀仪式中,正是面具承担起人神之间的通联,起到了“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的装扮效果。在巨大的面具上刻画表情符号,用夸张的手法来演绎神,越发让观众产生敬畏。
土黄面色、阔口大耳、面部祥和。

武安傩戏中的面具。河北日报记者白云摄
2024年12月27日,武安市固义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武安傩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增旺从自家二楼的道具箱里,小心翼翼取出一个红绸子包裹。轻轻解开系扣后,他虔诚地捧出一个面具。
“这是《吊四尉》中的四尉面具。”李增旺说,武安傩戏面具包含关公、城隍、判官、探神、大头和尚、黄虎等,分属人、鬼神及动物序列。
这些面具,总体来说面部周正、浓眉大眼,即便是代表邪恶的黄虎,也没有凶猛感,反而有些呆萌。面具抓住人物或动物某个动态面部表情,加以放大,或憨厚或凶悍,或幽默或严肃。它们附着着固义村村民对神鬼的朴素理解,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时,农民完成驱鬼除祟心愿的简陋道具。
李增旺收藏的面具由本村村民制作于1985年,原料为麻头纸。制作这套傩戏面具的工匠去世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武安傩戏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马增祥就成了目前唯一会制作面具的人。
1月17日,武安市马增祥家中。装满沙子和麸皮的布袋被4根木条夹在其中,马增祥用铁丝勒紧这一组合,并将它们固定在旋转的操作台上。屋外,从固义村挖来的生土已经和麦秸秆充分混合,稍一凝固就被铲刀铲着糊上简易的模具。原本圆柱状的泥坯逐渐有了模样——眼睛微凹、嘴巴微张、耳大鼻平、头戴官帽。

1月18日,武安傩戏传习所,马增祥正在制作傩戏面具。河北日报记者白云摄
固义村村民设计制作的拙朴面具,自然是从他们的生活中来。在学者眼中,武安傩戏面具“将超现实主义浪漫与想象力植入拙朴的农耕文明”,但大致以人面为基础,对鬼神、动物进行人格化刻画,制造出大家熟悉又陌生的各种角色。
这些想象出来的面具造型并不是武安傩戏最初的样子。据李增旺回忆,他小时候,村里的面具原料为树皮,在上面刻出嘴眼,用绳子勒住佩戴,更具原始感。
树皮制作的面具并没有留存,但河北博物院展出的中国最早的陶面具或许能带给我们些许想象。这件出土于易县北福地遗址的面具,夹云母黄福陶质地,人面弯眉细眼,直鼻宽口,微含笑意。面具四角都有孔,专家推测是进行傩仪表演时用来穿绳佩戴的。
武安傩戏面具也穿绳,这根绳不是系于脑后,而是演员用牙咬住,用于在激烈的表演中固定面具,以防来回晃动。
马增祥拿出他制作的绿脸小鬼面具,宽大的面具内部填充了很多泡沫,防止过硬的面具磨皮肤。
这些颇具祭神意味的道具,原料都来自质朴的生活。
马增祥家地下室,粗糙的麻头纸韧性十足,任凭两手抓扯也不断裂。堆放的粗白布,剪碎后和纸混成纸浆。在纸浆中掺入胶水增加黏性,一层层刷在干透的泥坯上,厚度达0.3厘米时静等纸浆风干、倒模,就做好了武安傩戏最重要的道具——面具。
地下室墙上,挂着粗硬的马尾毛和理发店买来的头发。马增祥用手捻着马尾毛说:“做赵公明的翎羽,这是最适合的材料,耐用又支棱,做出来最好看。”
这些简单易得原料制作的面具,用红青黄黑绿等颜色装扮出不同角色:橙黄色的寿星、土黄色的城隍、红唇绿脸的小鬼、《吊掠马》中忠义的棕脸关公、《吊黑虎》中勇猛的黑脸赵公明等。
跨越数千年的面具,是傩戏原始表达的具象化。这些古朴又灵动的设计,浸透着浓郁的燕赵文化,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刻下永不褪色的精神徽章。
傩韵铿锵,原始戏腔跨越古今
“嘚不咚,嘚不咚,嘚不咚……”急鼓骤起,演员登台。
主角白眉三郎踩着鼓点大退步出场,即使退到了台中间,还是以背示人。锣响鼓脆,气氛紧张,正当观众大气不敢喘,演员猛一转身,等待中的亮相却是演员用手中的白布继续遮挡面部,直到又做完一组动作,才正面示人。
1月18日,《点鬼兵》在武安傩戏传习所门前上演。
“这是傩戏作为敬神戏的特色,演员饰演的神迟迟不让观众看到正面,就是在铿锵的音乐中强化这种神秘感。”邯郸市群众艺术馆原副馆长杜学德介绍。
傩戏中戴面具的神灵出场,和其他戏剧角色出场时先来个漂亮的亮相不同。他们在出场过程中反复设计,吊足观众胃口后,才在突然之中亮出面具造型,将所饰演神灵的神秘和威慑力发挥到极致,实现一举惊四座的效果。
面具,是武安傩戏登台演员中有无唱词的“分水岭”。
“手拿铁棒过江河,借尸还魂铁拐李。”1月17日,20岁的潘雪瑞清唱了《开八仙》中铁拐李的唱段。
七字一顿,对仗押韵。武安傩戏的唱词浅显易懂,用武安方言抑扬顿挫唱出,外人很难分清是唱还是念。傩戏唱腔对技术要求不高,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即使完全听不懂词意,也会被一种乡音的真诚和质朴打动。这种有节奏且押韵、听来熟悉又上口的特点,让武安傩戏被称为“河北土话剧”。
当潘雪瑞饰演黑虎时,面具一戴,角色就只舞不唱。《吊黑虎》《吊掠马》中,先期出场列队的土地、五道、绿脸小鬼等配角,更是一言不发。
关闭听觉表达,只传达视觉上的震撼,在表演中通过一增一减,强化面具角色的神秘性,让观众看后“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在杜学德看来,武安傩戏处处用心、处处设计悬念,无非是拉开所演角色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烘托神,体现尊崇神。

2月9日,武安傩戏参加武安市2025年元宵节民俗文化巡演。丁建宇摄
最终由佩戴面具的神,协助村民通过祝寿、祭虫蝻王、祭冰雨龙王等仪式,传达他们希望“飞虫远去,百谷告成”“冰雹远去,甘露均调”等生产生活中的美好心愿。
这一强烈的敬神意味,让武安傩戏区别于行当齐全的传统戏曲,以生为主,净次之,丑、旦行做配角。
《司马懿观山》中的司马懿、《擒彦章》里的王彦章、《虎牢关》里的张飞,都是净行。丑行和旦行处于绝对从属地位,即便需要出场,也只有寥寥几句——《长坂坡》里的甘夫人只有4句唱,《过五关》中的糜夫人更是一句唱白都没有。
武安傩戏虽有唱念做打,但并没形成严谨的戏曲程式。这种原始自然的表演,在乡间街头、田野里上演毫无违和感,更显朴实无华。
《吊四值》《吊四尉》中,四值和四尉上下马的动作几乎就是照搬生活,举鞭绕场、弓步前行,没有难度技巧。
武安傩戏武戏很多,但武打简单。赵公明打黑虎,一个鞭击就结束战斗。三国戏中最具观赏性的主将对打,也仅仅是一个来回就胜负已出。
这些看似简单的戏剧表演,在鼓锣钹镲的烘托下,却丝毫不减感染力。
磨得锃亮的鼓槌在牛皮鼓面上击出沉闷的声音,配合着清脆的镲、短促的锣,敲出了一组武安傩戏急鼓曲牌。
1月18日,武安傩戏传习所成立9周年演出现场。第一次观看武安傩戏的观众可能都会吃惊,伴奏的只有大鼓、小鼓、大锣、镲等打击乐器,没有弦乐。
“武安傩戏的伴奏一般需一鼓、三镲、一锣。但这少量的乐器,能组合出轧鼓、上场鼓、急鼓等30多种曲牌。”武安傩戏鼓手李金钟介绍,乐师们通过不同音色、音量的配比,简单多变的节奏,以及力度强弱的变化,渲染紧张、恐怖、欢喜的气氛,表达人物情绪。
甚至在配合行进式演出《捉黄鬼》时,壮汉用木杠抬着鼓走,鼓手随走随敲,锣镲等乐师跟随伴奏。
就是在这种简陋的演出环境,表演者根据场上演出需求灵活组合不同曲牌。鼓点密时,台上仅有一人也似千军万马,鼓点稀时,纵有百人演出也井井有条,使人深嗅到一种幽深、古朴的韵味,大有尧天舜日、金戈铁马的震撼之感。
这些在现代化浪潮中倔强存活的古老艺术,既是燕赵大地的精神胎记,更是华夏民族集体记忆的活态基因。武安傩戏的每个动作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永恒,不是对抗时光的侵蚀,而是让文化基因在传承创新中,完成跨越千年的精神轮回。(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相关
一场武安傩戏这样上演
活跃在全国的各类戏剧,大多由剧团组织,在各舞台表演也有一定的演出频次。但想看一场武安傩戏,却要跟着固义村的节奏,而且只在农历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三天。
2024年12月26日,记者来到河北省武安市固义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武安傩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增旺家,75岁的老人手里折叠着一张巴掌大的黄纸说,武安傩戏是否开演,要经过固义村一社三户(西大社、东王户、南王户、刘庄户4个庄户社)的商议,并请神来决定。
1985年恢复至今,武安傩戏也不过演出了十几次。
一旦确定演出,这张黄纸被裁剪成食指长的纸条,由同时担任武安傩戏大社首的李增旺写上“定于西大社请”,邀请东王户、南王户、刘庄户各社首组织分工。一社三户又下设柳棍、烟火等20多个社首,负责组织对应的演出环节。
一场声势浩大的武安傩戏,多时有近千人参与,几乎占到固义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传承方式是武安傩戏在低频率演出中保证品质的根本。武安傩戏中涉及的主配角乃至烟火、服装、化妆等各工种,除了黄鬼一角,都通过父传子,在家族内部传承。
代表邪恶的黄鬼,在武安傩戏中是一个人人厌弃的角色。以至于每次演出时,即使高价雇外村人来演,都很难找到演员。
但村内,不管是道具组织还是登台表演,村民们都没有报酬,甚至连每年演出时的费用都曾由全村众筹。
“是信仰让我们做这些事,我们毫无怨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武安傩戏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马增祥说。这种虔诚的信仰,保证了武安傩戏各环节各工种的代代相传,让这项古老表演即使中断过多年,也始终没有失传。
村民们并不在意外界的认可和外来观众的多少,他们更关注能否通过演出达成祈求顺遂的心愿。(文/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